网上有关“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在我接触社会人类学的那天起,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人类学既然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那么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是关于人的研究吗?专门研究社会的社会学不算是关于人的科学吗?而这样的困惑,即便时至今日也常常会被人提及质询。但依我看来,人类学在他产生之初,其实是有包打天下的壮志雄心的。他以研究人为自己的职责,作为自己的学科边界。但在逐步的发展、成熟过程当中,他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领域和视野:他要通过观察和研究他者的生活方式来理解自我的习惯与风俗。而这一点的确立,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学科演化过程的。社会人类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07年剑桥大学聘任弗雷泽为人类学教授的聘书上。而要溯及这一词汇的出现,则依旧要回到人类学的童年时代。那时的人类学以体质人类学研究为主要方向。但是人类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影响人的进化和发展的不仅仅是生物方面的因素。知识、信仰、技术、法律、道德等等,都对人的进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一批专门研究人的文化层面的学者,主张从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人。这一流脉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它分为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而其中的第三个分支又曾经被称为成为民族学。名族学在英法等国的发展中,与社会学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成为社会人类学。而社会人类学中,也存在着视角的区分。尽管人类学越来越脱离那种非社会、非人类的自然科学轨迹,而转入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来寻求解释。但也由此分为两派,一派注重不同社会、民族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创造性的研究和发现。另一派则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某种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种争论今天也存在,而且我觉得日后也必将延续下去。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争论的核心不过是对于文化具有相对性还是普遍性的观点不同。而人类学家所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在把我文化相对性特质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大同,也即是一种沟通微观与宏观的综合视角。至此我们或许会简单认为,社会人类学不过是人类学分支中一个流脉。但是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如此的。因为社会人类学,或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其实是作为现代人类学的核心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则需要理解人类学从近代向现代的那一次棺盖却难以论定的转变。知识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科学有的时候恰恰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人类学从产生到发展深深的引证了这一结论: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是与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几乎同步形成的。甚至在某些问题中,人类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张目。而在这样的学科旨趣背后,则是进化论观点的作用。这一理论来自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社会的进步看作是一种匀速行进的必然,并且认为凡是同西方生活方式不同的,都是落后的,尚未进化的。因而作为上帝的文明子民有义务帮助未开化的兄弟。但这一理论的缺陷也恰恰在于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民族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社会的演进都是必然和匀速的话。因此,针对这一问题,人类学思潮中又兴起了传播论观点。他们认为文明的历史是文明逐步分化成不同个边缘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文化的衰退过程。他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空间上文化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的问题就是这种理论存有文化等级秩序预断的观点,并依旧把西方文明作为最高的核心。在经历了以上的两股思潮之后,人类学进入了二十世纪。此时两位奠基人的出现,使得社会人类学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人类学,并进而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的核心。第一位便是马林诺斯基,他为社会人类学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探索领域。马氏认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一定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入的考察,进行实地研究。他反对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不同于己的文化主观预断,主张移情式的理解当地文化的细微之处。而他通过田野调差研究所撰写的报告文字,便是日后成为社会人类学主要方法的民族志(ethnography)。另一位奠基人则是同马氏处于一个时代的布朗。在布朗的观念里,社会人类学等于比较社会学,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情况是不能够具有普遍性的,因此主张不要停留于西方社会的研究,而要勇于走入他者的世界:两相参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社会科学理论。而在分析视角中,布朗主张看待社会不仅要看他的外观,也要注重分析它的结构。因为内部的结构决定了外部的表现,而内部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作用,有对于结构本身具有功能。日后这一理论被我们通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而从此时起,社会人类学有了他成熟的方法、比较有效地解释理论范式,从而日益成为了当今人类学的主流。而在这两者中,永远变动的是理论范式的思潮,相对恒定的则是民族志这一比较成熟的方法。这一方法之所以恒定,是因为他体现了人类学的实质:他者的目光与好古之心。他者的目光,老师曾将之称之为离我远去的艺术。是的,这是一门艺术。因为社会人类学本身要求我们走出自己所在,勇入他者的世界。在另一片天地中反观自我的生活。而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超越自我勇气,追寻人类道统的责任和一份对于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可能性、多样性的追寻。一名人类学家,他要主动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到达一片非我的世界。在这里运用客人的目光看待周遭的万象并进而超越自己的文化,超越自己的惯习,领略他人的不同从而最终超越自我为主的心灵,达到对于自我文化与生活的反思。前辈马林诺斯基曾在的日记中流露出这样一种工作的苦闷与单调。而我们可以设想,一名人类学家,他需要怎样的才华与学识,怎样的勇气与担当才能够真正做到在熟悉的世界中将自我剥离,在他者的世界里回归本体?老师曾经告诫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彻底的剥离。而我以我的经历认为,一名社会人类学者就需要从这种不可能中探索最大的可能性,尽可能的去看清我们习以为常到已然忽略的另外的世界。人类学家都是有好古之心的。这并非是现代性下的转变所带来的思乡之情,而是自人类学产生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曾今的他自信满满的划分了三个世界,并向群氓宣告自己所研究的是未开化民族的生活。而伴随着进化论、传播论的式微,他者的目光方法的运用,人类学不再宣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是未开化的民族,但研究那些与现代化进程主流相异的民族与生活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在祛除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模式后,越来越强调在这些地区与民族中寻找到现代性的破绽和不足:在此,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也达成了一致前者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中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从与现代精神方枘圆凿中寻求人之为人的真谛。民族志这一方法集中地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结合:发好古之心的人类学家是不惮以最大的勇气和担当以他者的目光步入一片陌生世界的。在这里,他要至少熬过一年,要参与式的进入当地的生活,以被观察者的角度来思考、劳动、生活。这种主位的视角甚至要求他不得不精通一门当地的语言,或者是用一些漂亮的小伎俩以便得到自己所想要的情报。而这一切的付出的报偿是值得的,因为他的的确确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另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记得在念书的时候,读书会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两本书:莫斯的《礼物》还有特纳的《仪式过程》。我虽羞赧于报告自己的体会,但却认真的体味了书中的内容。时光已过,具体的细节我已经遗忘,但是我仍然记着,这两本书在告诉我社会人类学家眼中的社会,不仅不同与社会学家,甚至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莫斯说,社会就是物的流通,在物的流通当中人的灵魂附着于其上,似乎古语礼轻情意重在此有了经验意义上的支持和论据。特纳说社会就是仪式过程中人与人的融合,在每一个仪式过程中,人沟通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界限,对于仪式纯粹的投入,使得一个社会得以展现。在这里,我似乎又看到了孔子所谓周礼的社会涵义。这一切给予我启发,也使得我明白,一门社会科学的学问是一定要落实到本土的,是需要接地气的。而这一工作其实早在人类学在中国落脚便开始着手行动了。中途中虽然遭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扭曲,但是社会人类学毕竟在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成绩:一个层次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当然,这两个研究背后的理论预设依旧可能存在传统现代二元分立的弊端,但他们的成绩无疑为世界社会人类学研究贡献了极为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一套理论,一种思想或是操作方法,要想回归于本土,最大程度的减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就应当批判的看待它。作为社会科学重要一脉的社会人类学尤为如此,我们不仅要发掘各派视角和方法得以产生的条件与时代背景,更要在宏观层次上把握这门科学的旨趣之所在。易言之,我们要想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进步,就要了解人类学的终极关怀所在。多年前,老师曾经教导我说人类学是一门善待他人,让人成为人的学问。而伴随着我多年来的实践,无论理论思辨还是经验研究,我深深感到人类学确实如此。用更简练的话语来概括,人类学就是一门旨趣于仁的学问仁者,爱人。在研究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了解人、理解人并进而实现人的相互沟通与和谐。因此,用善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以仁者的目光去关怀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学科职业伦理的问题,也是这门学问安身立命之本纳粹的研究不可谓不精深,但其最后下场世所共睹,实所共鉴。而这门学问也正如夫子心中的仁一样,他未必会给我们带来金钱、财富、荣耀、地位、权势,但是他给了我们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目光:在他者的目光里,我们勇于自觉疏离于这个熟悉的世界,为了人类另外一种可能性与多样性而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是艰辛的,难以取得突破的,但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这里弘有了空间上的意义我们为了这份担当与责任,应当在他者的世界追溯人类共同的道统;毅充满了时间上的意涵在他者的世界里,我们并非浅尝辄止的,而是要深入进去,坚持不懈。当然,我们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无所获的,或者是错误的,更有可能是若干年后又被新的研究推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追寻和探索是虚无的,因为这门学问仁爱的旨趣让我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善待他人的同情式理解,充满智慧的朴素民族之方法等等的一切给了我们多彩的研究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去损人利己,不会支配他人,不会斤斤计较,却会收获友谊、收获智识,收获来自于远古的人类生命本能的悸动。仁者,爱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如此的学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人类学是有着如此要求的学问。
我国的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有多少年的历史
诗经》共收录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 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共收集了305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孔子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 駉》中说的:思无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诗人的言语有赞美的,有讽刺的,对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语言来赞美它,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丑恶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语来讽刺它,以惩罚人的恶念。都是要提起人们善良的念头,除去人们丑恶的思想,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如果人心的每个念头都是纯正的,没有被私欲邪念扭曲的,那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充满了善行,而没有恶行,充满了被赞美的行为,而没有被讽刺的行为。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也不过是为了劝善惩恶而已,因此由思无邪三个字,足以概括《诗经》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学人务必了解,应该将功夫下在“慎思”之上。
作者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内文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一说王者采诗。《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还有朱熹在《诗集传》也说过:“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而且在《汉书·食货志》、《礼记·王制》、《晋语六》也有类似的记载。
后期整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的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由于《诗经》写作年代距今久远所以对其作出绝对确切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故古人有云“诗无达诂。”“诗无通诂。”
编辑本段详细目录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小雅·鹿鸣之什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 小雅·鸿雁之什
小雅·节南山之什 小雅·谷风之什 小雅·甫田之什
小雅·鱼藻之什 小雅·都人士之什
大雅·荡之什 大雅·文王之什 大雅·生民之什
周颂·闵予小子之什 周颂·清庙之什 周颂·臣工之什
商颂 鲁颂·駉之什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距今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诗经》是经典的经典,唐人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推崇《诗经》,独标风雅比兴,即刘氏所谓“唐代特异拟经之风”在诗歌中的彰显,这一现象已为学者熟知。就鉴赏而言,历代诗论中,有一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宋代以后的学者,在品鉴唐诗的时候,每每与《诗经》相比附,揭示两者的渊源关系。
而对其他时代的诗歌却非如此普遍。明代杨慎深谙三昧:“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且举唐人闺情诗云:‘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即《卷耳》诗首章之意也……又云:‘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即《卷耳》诗后章之意也”。
(《升庵诗话》卷八)与宋诗相比,杨慎不仅揭示了唐诗与《诗经》的神似之处,说明唐人以《诗经》为模范的实践的成功,而且,指出了唐人“以作诗来解《诗》”的诗性的或艺术的阐释形式。这是唐代《诗经》学“诗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以唐诗来解说《诗经》,为我们研究唐代《诗经》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扩展资料:
唐代《诗经》学诗化的过程,不仅融进了唐诗的血液,而且参与了对盛唐气象的陶铸:
其一,唐诗正统化。唐代《诗经》学由经学转进为诗歌,儒学蓬勃向上的功业观使得唐诗得到当时社会以及后人的普遍认同。
其二,诗人文儒化。唐代从经、文对立两分(孔颖达、李白),到文儒合一(杜甫、韩愈),经、史、文统一于儒学,儒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初唐经学家与诗人往往不能兼得,但是中晚唐以后却逐渐改观。
其三,官僚诗人化。诗歌正统化,作诗不单是时尚,也是走向仕途必备的技能,诗人成为官僚的基本标识。
其四,诗学范畴化。唐代以标榜风雅、比兴、六义为核心的范畴运动,是《诗经》学诗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唐代诗学范畴化的必然。
其五,诗人群体化。诗赋取士,《诗经》“可以群”的功能在唐代复盛,激发诗人的兼济之志,促成了唐诗的开放性、功业性特征。
百度百科——诗经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新华网——唐代《诗经》学和唐诗的形成
关于“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佟佳明月]投稿,不代表海宁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ap.hnjsjm.com/hainin/874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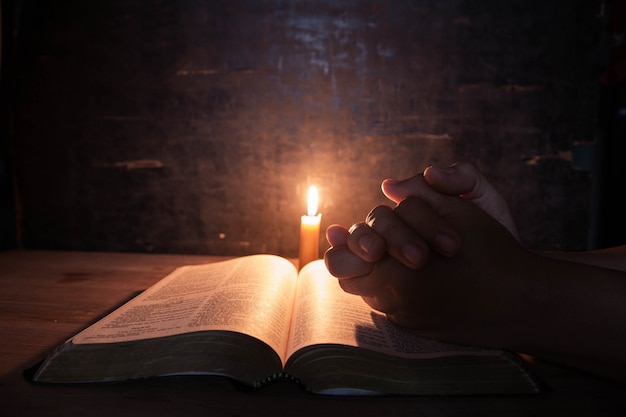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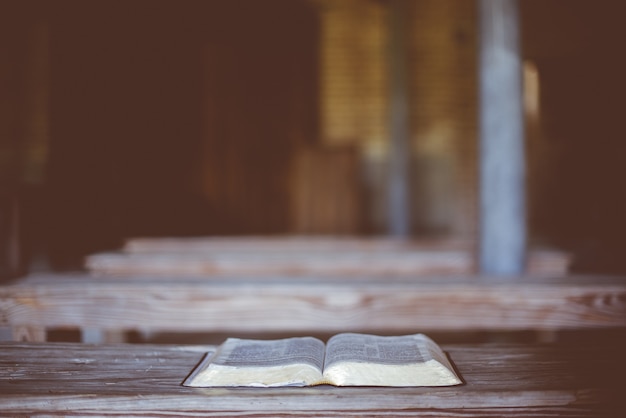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海宁号的签约作者“佟佳明月”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
文章不错《我所理解的社会人类学是什么 ——拟一位社会人类学家的自述》内容很有帮助